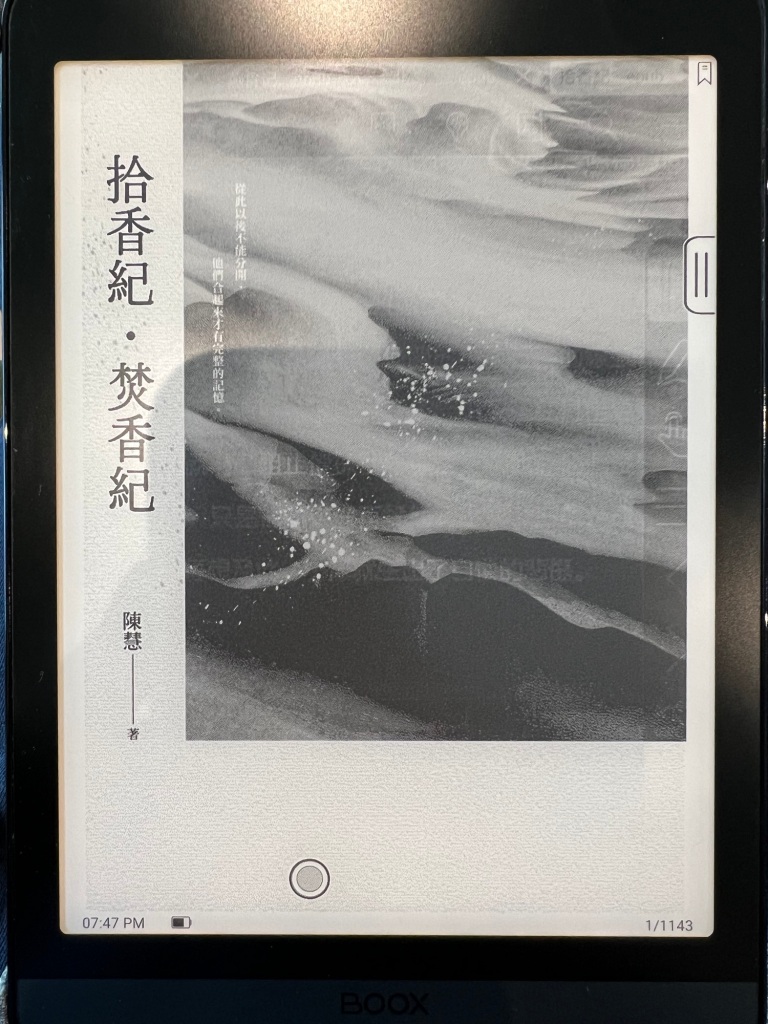錢鐘書的《圍城》 有一句名句「婚姻是一座圍城,城外的人想進去,城裡的人想出來」 。此話很真並且可以代入很多事情, 可以是婚姻也可以是移民。
很多香港人想來英國,然而又有很多英國人恨不得離開英國,定居在葡萄牙,西班牙,愛爾蘭,甚至泰國。 人口全球化地互相流動是一個趨勢,水向低流,而人也未必往高處看,因為以全世界來說,哪個地方叫「高」呢? 很現實的問題、高與不高視乎口袋有多少錢。 情況尤如香港人傾向回深圳消費,港幣$100在香港可以買到什麼,同是港幣$100 又可以在深圳買到什麼,英鎊£5 在倫敦來說,實在高不成低不就,可以買一個Gail’s 牛角包, 而大約又是英鎊£5(歐元€5) 可以在西班牙的Malaga 喝杯咖啡加牛角包了。
小數怕長計,生活上來說當然是咖啡加牛角包的滿足感比只有牛角包為多。就是類似的生活滿足感,西班牙比英國更平,更靚,更正,所以很多英國人退休也在西班牙居住, Barcelona 罪惡率高,那麼西班牙的其他古城如Malaga或Cadiz就平和多了,人口小,生活簡單,口袋剩錢多了,生活質素又上升了。人望高處下,那麼何處才是「高」 ,何處又是吾「家」 呢?
在英國生活有個優勝之處,就是英國跟歐洲其他城市的距離很近,所以很多英國人一有長假短假,就會往西班牙,葡萄牙等地走。 旅遊其一, 久而久之必定也會想過能否定居呢?
生活在西班牙,可購買的能力及生活質素比倫敦好,而當你再去葡萄牙的里斯本,就更覺里斯本還要好。新認識的英國朋友說:「里斯本好嗎? 里斯本太貴了,去葡萄牙的南面Algarve吧,100萬歐元在里斯本的市中心,只可以買層2 房1 廁的舊樓,但在Algarve,70萬歐元可以買個全新的玻璃幕牆又有太陽能板的3房4 廁特色別墅。30萬歐元可以買市中心2房2廁的新樓了。」 人望高處,水向低流,全球人口互相流動正是如此。
上星期我又去了里斯本, 像男人愛上女人般,久不久就得見面,大街小道應該怎樣行一早已印在腦海。 由奧古斯塔街凱旋門(Arco da Rua Augusta) 直行,第一個街口左轉,一路直行至盡頭,見到橋底咖啡廳就是正確方向,沿路多行2 個商店就是Stetson Hat shop。
Stetson 是一個有159 年歷史的美國品牌,也就是美國牛仔Cowboy hat 的始創人,所以cowboy hat 又名Stetson。一個品牌能跨越世紀當然殊不簡單,從前做生意可能比較簡單,講求質量及設計就能雄霸市埸。 今時今日的生意,又要壓低成本,又要求質量,同時也要與淘寶或Amazon 的潮流抗𧗾,人家要復制設計, 簡直易如反掌。
第一次認識Stetson 帽子是在Fonte Norte Do Rossio (羅西烏廣場) 外的一間百年帽店名Chapelarias Acevedo Rua, 初時被其古老氣息的裝潢吸引,入內發現客人頗多,店員就只有2個老女人。在外國購物文化不同香港, 從前我在百貨公司打暑期工時,就算正在招呼客人,也會在客人試身時,騰出時間照顧其他客人。 在外國則完全是兩碼事,they would only do one thing at one time, 處理完一個客人,才會接待排頭位的另一客人,所以想看或試戴帽子的話,就一定要耐心等待。

那回等了15分鐘也未輪到我,就乾脆不等,決定去附近咖啡室喝咖啡吃葡撻。 臨走前把想買的帽子用手機拍下,然後在咖啡廳上網搜尋。網絡世界的美好就在彈指之間,九百六十轉,為你搜尋另一間附近店舖。由google map 引領下,我找到Stetson 的專門店,
走過未行過的斜坡小路,推門而進是充滿現代設計的帽店,店內有2 個年輕店員,男的戴上品牌帽子,型格非常,女的身穿稱身十足的西裝外套配牛仔褲, 笑容可掬,正在整理貨品的她,跟我打個招呼,我遞上帽子的照片,她就即時拿出我想試的種類。
我看見從前的自己, 我就是如此的殷勤及對產品完全熟悉,充滿自信的為客人推銷。那是自由行還未大行期道的香港,一個早上,才HK$250 一條男裝褲,我就可以賣出10幾條,早上HK$3000的生意額,是全部門最高的,顧客絡繹不絕的話,輕輕鬆鬆又一天,生意肯定過萬。 當年,我的掃把(supervisor) 有個行內術語,過萬即過山。 下午6:00,她會走過來:「妹,過咗山未?」 「有前途呀下,工作辛苦嗎?」我告訴掃把 :「只要你決定把事情做好,沒有什麼辛苦的,都是個過程。」
眼前的葡萄牙人叫Rita, 言談間得知羅西烏廣場外的百年帽店是她先祖父開的, 她大學畢業後就在那店工作11年,怎樣為客人選適合的帽子也是老店的老員工教她的。 此Stetson 的店舖是自營店,跟美國總公司拿貨, 可把季度剩餘的貨存退回,再換新貨,
可能經歷相近,自此我和Rita 成了一個遠方朋友, 每次到里斯本的話,我定必會到其店鋪探她,順便買帽子。這次在里斯本,恰巧遇上風暴,暴雨從山坡石級衝下成了街道瀑布。我從「X」 (前身Twitter) 看着視頻,看到熟悉的道路,此次不知能否探望Rita。翌日,我頂着烈風,沿著石級而上,到達店舖才早上9:30, Rita 看到我,滿心歡喜,即時開門迎接我進去。
互相擁抱,互相問好後,才知道她昨天才從羅馬旅行回來,如果她遲一天才起程回里斯本的話,我們就緣慳一面。 Rita 說她的店舖上個月入夜被打劫,兇徒打爆玻璃而入,偷走櫃枱€80 就走,損失不大,就當破財擋災。 她續說里斯本的冶安差了,但還是比很多大城市為好, 小偷都是機會主義者,他們沒有其他方法為生,就只能搶,劫和偷。
葡萄牙剛結束大選,新政府上埸,不過應該經濟問題依舊。 里斯本跟錢鐘書的《圍城》一樣,人來人往,有人辭官歸故里,有人漏夜趕科場。 歐洲富人,或亞洲人都貪圖里斯本的高質又低成本的生活,不斷帶來資金在里斯本置業定居,慢慢地樓價被推高,生活成本也因此上漲。 本土人在人工遠遠追不上生活下,不得不離開里斯本,因此本土人口被邊緣化,土紳化問題/ 城市重生(gentrification)把里斯本的人口換血。 真正的里斯本的口袋沒有錢,里斯本的大小生意都由自外來人或遊客的消費支持。 簡單來說沒有外來資金,沒有遊客的話,里斯本的經濟齒輪就如履泥途。
Rita 的生意也是80% 來自遊客,20% 是本地人。 她說葡萄牙人的最低工資才€3, 稅高,生活成本又高,怎有餘錢? 我說:「相對地,英國的最低工資£11, 人工高,稅高,生活成本高其實也是所餘無幾。是全球化問題吧。」 說完此話,我才恍然明白此乃世界的遊戲規則,其實大家也是沒有多少錢,不過爛船總有三斤釘下,大家就利用那三斤釘,去找自己的「樂土」 ,也就是水向低流到人間「高處」。
若然殖民時代的西方世界以征服他國作為經濟發展, 當今世代,「殖民」的方法就是以gentrification 來代替。 名義上為地方提升價值,實際上也只是「佔領」及「被遷出」。里斯本如是,香港如是, 倫敦亦如是。 全球面對的問題大同小異,只是深淺之分, 倫敦的gentrification, 有出有入,有人離開的同時,亦有很多人進來,因為倫敦畢竟還是經濟機會處處。 香港的一部份人移民了,一部分人北上消費,就型成空城化。
世界都是錢作怪, Rita 說可能因為本地人被邊緣化,里斯本的左派勢力逐漸抬頭,不過另一方竭力扺抗。愛國主義當道是世界的一戰及二戰的開端,我又想起Hamburg, 2個月前漢堡的市政廳廣場萬人空巷,就是為了反對的極端Fascist 政黨AFD 抬頭。
看來,經濟發展,本土邊緣化,本土意識抬頭,愛國主義, 政治體制互相碰撞下,世界戰場除了無辜的烏克蘭外,還有我們住的地方及旅行的地方。